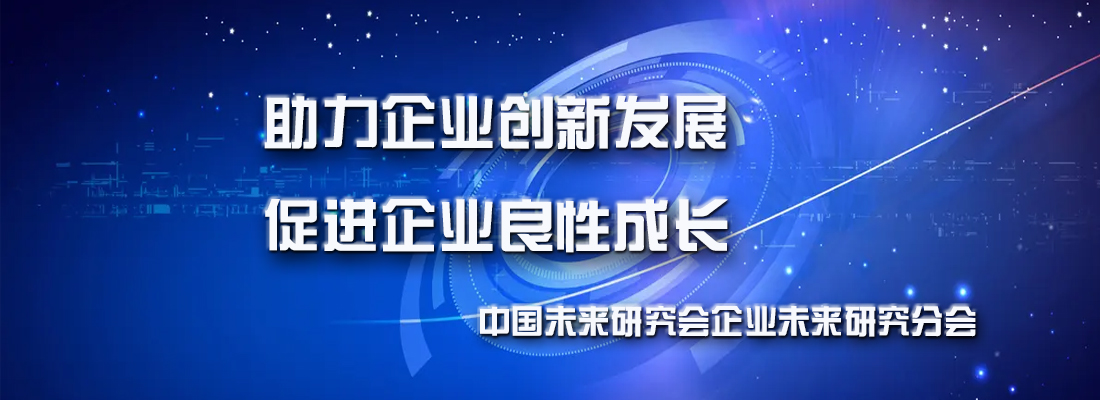我在中南海度过的少年时代
明成祖赐名万岁山,但明朝只存在了267年
中南海是新中国的政治中心,原来是皇城西苑,由北海、中海和南海三海组成。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时,一开始住在北海的琼华岛上,即燕京八景之一的“琼岛春荫”。后来开始大规模的元大都营建工程,他采纳水利专家郭守敬的设计;从玉泉山引水经过瓮山泊(即今昆明湖)流入高粱河,汇入积水潭,后再流经都城接通惠河一直到通州(今通州区)。河道经过今天的北海和中海附近。当时这一带水天一色,湖水浩荡,故名“海子”,北海、中海、什刹海三海则因此而得名。
那个时候,北海和中海都在皇城宫苑范围,定名为“太液池”,这也是燕京八景之“太液秋风”。太液池两岸建起宫殿,东岸的宫殿为“大内”,就是明、清两代紫禁城的前身,西岸分别建起隆福宫和兴圣宫,分别为皇太后和太子的住所。
明朝永乐年间,太液池被从大内划出;称作“西苑”。为使宫苑扩展,又开始开挖南海,让太液池水流经承天门(今天安门)前的金水河,并且把挖出来的土堆成了“万岁山”(今景山)。历史似乎在恶作剧;明成祖挖土堆了万岁山,给崇祯皇帝安排了上吊的地方;慈禧挖瓮山泊堆了万寿山,结果断送了大清260年的江山。中南海的瀛台,也成为囚禁光绪的地方,令人感叹不已。
在清代西苑范围内,中海西岸只到紫光阁和时应宫。西苑外的皇城根,是平民居住的地方,康熙将西苑皇城外一块儿地方赏赐给法国传教士建“救世堂”。过了200年,西太后慈禧却耿耿于怀,让善于办理洋务的李鸿章重金赎回,此后又征收蚕池口附近的民居,从紫光阁以西又建起围墙,把今天的西华门以西的地方全部圈进西苑的范围,这就是今天中南海北门到西北门一段围墙是灰色而不是红色的缘由。一直到今天,虽然中南海的外围墙经过多次粉刷,但仍然保持了历史的原貌。如果你没注意到,现在就可以去看看。
到了清末,太液池的格局基本形成,金鳌玉虫柬桥分割北海和中海,蜈蚣桥划分中海和南海。而中南海主要是慈禧休息的地方,她的寝宫叫仪鸾殿。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这里曾是他们的指挥部。后来不明原因失火,烧死一德国将军,德国统帅瓦西德侥幸逃生。慈禧回来后,仪鸾殿又重新修复,改叫怀仁堂。民国以后,清帝逊位,袁世凯不敢公然在紫禁城称帝,就住进了中南海,办公在勤政殿,吃住在春藕斋,并把勤政殿改称“中华宫”,在这里做了83天皇帝梦后一命呜呼。
以后北海和中南海被分别辟作两处公园,除中南海北区有一部分是国民党时期的北平市政府的办公地点外,其余都对游人开放。
在中南海里开一亩三分地种庄稼
1949年北平解放初期,中共中央决定定都北平并改名为北京。但在办公地点未清理好以前,暂住香山,对外称“劳动大学”。最早进入中南海并主管接管工作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以及周子健等人。成立中南海办事处以后,周子健担任处长,布置科有位叫钟灵的人,就是当年在延安写标语时,把“工人”的“工”字写成“互”而被毛泽东挖苦过的那位先生。
在周子健的指挥下,经过清淤、排雷、修房。一切安排就绪。周总理每天都在中南海和香山之间奔波,可是毛主席就是不肯搬进中南海,据说还勃然大怒,说住进去会像皇帝老子那样遭百姓的唾骂。
今天中南海的范围已经确定:南端是新华门,往西沿府右街北行,是中南海西门,再北行是西北门,也叫国务院西门,过此门后沿围墙(灰色)东行是北门,正对原北京图书馆,又叫国务院北门。继续东行过金鳌玉虫柬桥,过北长街、东华门、南长街从警卫局大楼往南再西行,到新华门。
新华门原来叫“宝月楼”,在南海南岸,传说是乾隆皇帝为了取悦香妃而建。后经专家考据,是乾隆在南台(今瀛台)南望,嫌南岸直长,无蔽障,因此修建宝月楼,西侧同时还建有茂对斋,同豫轩,形成一组建筑,从此以后,宝月楼成为中南海南岸的屏蔽,也成为南端。
正对宝月楼(新华门)南海的北岸就是瀛台,往北有石桥连岸,登岸东面是勤政殿,原来是椭圆形大厅,左右各有两进四合院,袁世凯在这里登基作皇帝时,把大厅的中式方顶改成西式的圆顶,成为不西不中的建筑,文革后期,一位中央负责人让把勤政殿拆建成办公和住宿的地方,从此这座极具历史文物价值的建筑不复存在。
再过去就是丰泽园,清代文人文征明在咏南台的诗中写到:“西林迤逦转回塘,南去高台对苑墙。暖日旌旗春欲动,薰风殿阁昼生凉,别开水榭亲鱼鸟,下见平田熟稻粱。圣主一游还一豫,居然清禁有江乡。”文征明的诗虽然拍了皇帝的马屁,但说明当时的统治者为了显示亲民形象,不忘躬耕,在中南海里还是开了一亩三分地种庄稼。
这里是颐年堂,但是不搞一言堂
丰泽园是毛泽东进中南海后的居处,原来是周恩来居住和办公的地方。丰泽园也是中共中央筹备新政协,操办开国大典的中枢之地。据说毛泽东喜欢丰泽园,除了它是清禁(清朝禁地之意)中有江乡之貌的清雅,还有园名与他的名字契合:毛泽东字润之,而丰泽园又隐含“泽润生民”的意思。
丰泽园是一个古建筑群,大门为楠木所制,门匾棕黑漆底衬托着三个金字“丰泽园”,但不是乾隆御笔,而是一个擅长欧体的官员所写。进大门后就是颐年堂,本是皇上退居二线,颐养天年的地方,但毛泽东另有新解,因为这里经常召集会议,所以毛泽东告诉与会者:这里是颐年堂,但是不搞“一言堂”。毛泽东的湖南乡音,把“颐年”读成“一言”。
北平解放以后最早住中南海丰泽园的是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他住在颐年堂后院正厅,1949年4月中旬,周恩来从香山搬到中南海,住在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东房,后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也住进中南海菊香书屋的西房。
到了6月份,毛泽东正式进住中南海丰泽园,林伯渠和周恩来相继迁出。周恩来选择了西花厅,林老住在福禄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在丰泽园住过,毛泽东进住后,他的机要秘书叶子龙也住在院里,杨尚昆就搬出了丰泽园。
丰泽园旁边,是一处设计精美,环境幽雅的园林院落,名叫静谷,里面水榭池塘,莲荷飘香,太湖石堆砌假山,土坡处有一座木楼名曰:“爱翠楼”。再往西一点儿,就是“卐”字廊,其实是在水面筑起“卐”字形走廊,匠心独具,因其形而得名。刘少奇搬进中南海后,就住在这里,那是1949年8月的事,当时刘少奇秘密访苏,家已迁入中南海。
“卐”字廊后的宅院并不宽敞,但十分精致,正房只有三大间,中间的大房是客厅兼餐厅,另外一部分权作书房,两侧的房间则是卧室,刘少奇一家在这里没住多久,就搬到甲一楼住了。“卐”字廊后来的主人是中办主任杨尚昆和夫人李伯钊,杨尚昆在文革初期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搬出了中南海,最后的主人是陶铸,说来奇怪,这里是距丰泽园最近的居处,就是说是离毛泽东居所最近的地方,而它的三位主人都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中南海里差点盖起大楼
在静谷和“卐”字廊的北面,是一组宫殿和水榭构成的建筑群,叫春藕斋,这里游鱼戏莲,荷藻满塘,是中央领导同志召开较大型会议及娱乐的地方,通常是舞会或放电影。春藕斋直对居仁堂,这是一处中西合璧的建筑,地面挖出喷水池,廊桥架在上面直通大厅,居仁堂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办公地,但1955年以前这里是中央军委,总参作战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办公处。春藕斋结构在60年代进行过很大的修缮工程。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春藕斋在修缮时,木水榭被改成水泥和汉白玉的水上舞台,破坏了古朴清幽的风格,变得不伦不类,而居仁堂也被拆了,要建中办大楼,据说毛泽东路过此地,见状大惑不解,问道:“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主管人员自知闯祸,建中办大楼的事就此搁置,一直到文革以后,也没有音讯。
居仁堂西北角,有一排以福字命名的院落。1953年,彭德怀将军从朝鲜回国就搬进中南海的永福堂,它的前任主人是红军之父朱德。朱德后来搬到甲2楼与刘少奇为邻。永福堂的两位主人后来都迁出了中南海,彭德怀59年因庐山会议受批判,搬到海淀挂甲屯的吴家花园,朱德在文革中搬到海淀万寿路的新六所。
以福字命名的还有增福堂、赐福堂。中宣部长陆定一和副部长张际春分别住在这里,张际春上井冈山时就和毛泽东在一起,又是帮助毛泽东起草“古田会议”决议的军中大笔杆子,以后在西南军区做副政委,和邓小平、刘伯承一同坐镇西南。进中南海后他先后担任国务院文教办正副主任。可惜文革后不久病逝。而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写匿名信斥骂林彪,结果这对夫妻双双被押送出中南海。
居仁堂的西侧有一排小型四合院,名号是迎春堂,毛泽东的大秘书,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住在这里。他的下场众人皆知,不多说了,他的邻居则是另一位毛泽东倚重的大笔杆子胡乔木。
明清建筑群里有一组日式灰砖楼
中南海里还有一组引人注目的建筑群,是日式结构的灰砖楼,东侧靠北部是服务设施,人称西楼,20世纪50—60年代著名的西楼会议即在此处召开。西楼分三部分,大厅供跳舞和放电影用,兼作大会议室;北部用屏风隔开则是刘少奇、朱德的“特灶”,彭德怀回国后,也在西楼就餐。
与西楼为邻有两栋日式四层楼,全部是旅馆式格局,笔者就在这里住过几年,楼分南北,但称为前楼和后楼。最南面是东西两座三层小灰砖楼,叫甲楼和乙楼。也有称之为甲一楼和甲二楼的,我们根据楼宇的主人分别叫做刘(少奇)楼和朱(德)楼。小楼南北的草坪则称为草地和后草地。现在这几栋楼仍然是中央办公厅的办公地点。朱德同志的那栋小楼是中央政研室的办公地点。在朱德搬出中南海以前,刘少奇就离开甲楼,住到福禄居了。福禄居原来是林老(伯渠)的住宅,1963年林老病逝后,这里没人住,经过修缮。刘少奇从甲楼迁到了福禄居,这是一套两进的四合院,进门后拐到前院,一排平房是办公室和卧室。西边大一点的房子是会议室兼客厅,东厢房是工作人员用房,主要是秘书,警卫人员在这里办公。东侧有一个走廊通往后院。刘少奇的子女就住在这里。几年以后“文革”开始了,刘少奇向毛泽东提出离开中南海,率子女回乡劳动的要求。最终他还是被剥夺做人的尊严,化名刘作黄被押出中南海。
在游泳池,毛泽东度过了最后岁月
在福禄居的东面是大食堂,再往东就是游泳池了,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他的最后岁月。
在怀仁堂边上,有一排四合院,叫庆云堂,依次住着李富春、刘澜涛、邓小平和陈毅。邓小平1957年住进中南海,他住的院落叫含秀轩。
在怀仁堂的东面,住的是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与他为邻是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人王稼祥。王是中共元老,与夫人朱仲丽相伴为生,他们收养一女,可惜“文革”中与养父母反目,以划清界线为名,打了王稼祥,这使得王老夫妇痛心不已。董必武后来也搬出中南海,迁居圆恩寺,与杨尚昆为邻,但这是“文革”以后的事了。
紧邻福禄居的院落,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的宅院,他没有住在西花厅。周总理在西花厅住了27年,病逝于养蜂夹道的305医院。西花厅属于西花园的建筑群,也是清末摄政王载沣王府的一部分。1909年开始修建,主要有王府正殿、宫门、御道、银安殿、思廉堂,西边有大圆宝镜院,十洲尘静院和西花园。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担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袁世凯把这里作为国务院的办公地,1918年徐世昌当总统时,把国务院改为总统府,1924年执政府段祺瑞执政又将此地改做陆军部和海军部。后来这里又成为北平市政府的办公地。
周恩来住进西花厅以后,中南海北区成为国务院办公区。原来摄政王府的正门和上殿仍然保存,用作国务院会议室。原来十洲尘静院保留了假山和平房,另一处殿堂是周总理主持国务会议的会议室,现在仍保持原貌。
西花厅是座两进的院落,进门后一座假山,修竹丛翠,南北有一条曲廊,前院最高大气派的建筑是建在一米多高的平台上的前厅,是周总理会见并宴请宾朋的地方。平台下是花坛,种有周总理和邓颖超最喜爱的花卉。后院到正房就是周总理的办公室。办公室东侧是周、邓会见私客、用餐和休息的“多功能厅”,然后就是邓颖超的卧室,也做办公室用,她的隔壁就是周恩来的卧室,卧室和卫生间有内走廊相连。周恩来与中南海其他住户不同,是被疾病逼出西花厅的,但他深知他也处在危险的政治旋涡中,他曾经深沉的告诉工作人员,死后不要在他的脸上(照片)划“×”。
一个中南海,半部现当代史,斯人已逝,物是人非,但它凝固了一段历史,一段不能抹去的历史。●
我在中南海度过少年时代
种菜浇粪
朱德搬到甲2楼以后,在楼前的草地上种上了瓜果,楼后种了一些果树,主要是梨。春天一到,满树开花,轻风徐来,似白蝶翻飞。他又在楼后的过道搭起席棚,种上兰花。小时候我很奇怪:以朱德的功劳和威望,完全可以养尊处优,坐享其成,为什么要亲自辛勤劳作呢?后来才悟出一些道理,当时只是敬佩而已。
当时我父亲任朱德秘书。有一天,我父亲回到家里,情绪不高。妈妈问怎么啦,他说:“有件难办的事,二组(刘少奇处)对四组种菜浇粪有意见,说臭得很,告到杨(尚昆)主任那里。杨主任要我和老总说说。很难开这个口……”
工作上的事好协调,这种事却很难讲。我后来注意到,朱德再到西楼劳动,总让干部们浇稀肥,事后再盖些土。不知道父亲是怎么和朱德讲的。
后来遇到三年自然灾害,整个中南海都是种的瓜菜,警卫团还派部队去内蒙打黄羊。刘少奇家也有了变化,苹果、梨之类水果少了。我去找刘源,他们家招待我吃西红柿。反映朱家种菜浇粪的事,像没发生过的一样。
养兰送兰
朱德的兰花在中南海是出了名的。正好我父亲也懂一点儿兰花,而且一直喜欢郑板桥的字画,只是不大看得上板桥的人品,说他爱发牢骚。父亲常与朱老总在一起聊兰花。
朱德似乎命里和兰有缘:不仅有位为革命献身的妻子伍若兰(伍绍祖的姑姑,朱德是伍绍祖的姑夫),而且一生喜爱兰花。开始时比较原始。那年父亲陪老总到井冈山,两人散步时挖了些野兰花带回北京。还有一次四组去福州视察工作时,朱德指着一棵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说:“上面有兰花。”当地同志架梯子上去一看,果然有一丛寄生兰。在场者莫不交口称奇。
渐渐地,朱德种兰花成了气候,品种花色也多起来了。日本友人松村谦三送给朱德一本兰谱和一些日本兰花,我父亲把兰谱拿回家研究,因不懂日文,便和家人一道指日猜汉。然后又和朱老总商量,居然猜了八九不离十。于是,把个兰花养得幽香四谥,蕊馨叶茂。有一回,朱老总选了几盆兰花送到丰泽园,不知为什么,却被毛主席退了回来。
还有一件事:朱德给兰花搭了个席棚,买竹竿和苇子一共花了70元钱,父亲拿着发票到特别会计处报销,也没报销成。
我和妹妹:中南海里快乐的孩子
划船
中南海过去是皇家禁苑,民国年间被辟为公园。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进驻后,虽修缮多次,但格局未动,所以这儿成了不是公园的公园,是孩子们的天堂。毛主席住在丰泽园,他住所周围都在禁区之内。他家后面是中海,前面是南海。主席要划船,一般是在南海,大家不敢打扰他,就去中海划。
后来出了两件事。一天,一群新到中南海的青年干部休息时划船,在船上又拉手风琴又唱歌,不知不觉地划到了中海的南侧。警卫战士见状大惊,打手势让他们离开,可这伙年轻人正在兴头上,竟没发现。战士只好大声喝斥,船上人这才知道造次。灰溜溜地划走了。第二件事是我和几个孩子在中海边玩闹,不慎从一条大船上落入湖中,虽没出大事,却惊动了中直管理局,结果下了禁令。
不让划船,等于限制了我们的一大乐事。于是我们就想别的办法弄船划。比如求管理员法外施恩;再就是分散他注意力,偷船划,完事后把船往湖里一推,任其漂荡,但这后果严重。第二天大灶小灶食堂都会贴出告示,告诫家长严肃管束子女。调皮孩子的家长便会施以严厉管教。
一天,我和几个孩子又在码头聚齐,向管理员保证:一不划远,二不瞎闹,三不乱吵,四不到甲区。可他死活不答应,我们软磨硬泡,声音一高一低,加上旁边起哄的,谁也没注意到有人走来。这时管理员突然放下手中织网,起身恭敬地说;“主席——”我们也顿时鸦雀无声,愣了半天,大家才结结巴巴地说:“毛爷爷好”。
我记得,那天毛主席不像照片上那样面色红润,而是略显倦意,说话时露出的牙也不白。倒是笑起来和照片一样,宽厚而且慈祥。
他问:“你们是哪家的娃娃,在这里闹什么?”
我们怕给家长惹麻烦,都吞吞吐吐。徐业夫秘书和我们住在一起,就指着他认识的孩子告诉主席:“这是四组老沈的孩子,这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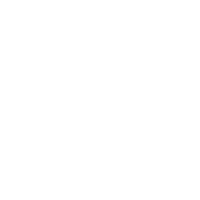
在朱老总家吃饭
主席问我:“你在这里闹什么?”我答:“没闹,就是想划船,管理员不让。”
主席问管理员:“为什不让娃娃划船?”管理员报告说,为了安全,管理局有规定,不让小孩子划船。
主席又问我:“你会游泳吗?”
我答:“会。”
“游得远吗?”
“远,能游到对岸。”
“那好嘛,你们就去划,船翻了也不要紧,自己游回来就行了。年轻人喝几口水没关系,喝水就学会游泳了,会了就什么都不怕了。”
孩子们顿时吵闹起来,纷纷说会游泳。管理员虽鼓起勇气解释,可毛主席却似乎想看看这帮孩子划船的本领。
我们得了鼓励,解开缆绳,上船划开了。在场的工作人员谁也没劝,管理员尴尬地笑着,只是看着我们为所欲为。
那以后,中海湖畔出现了两个浮船做的水上平台,供人在湖里游泳时休息。据说,毛主席也曾想到湖里游泳,但被管理局以水质为由,警卫局以安全为由(从北海大桥上可以看到湖中)阻止了。
1965年中南海实行“革命化”,划船和舞会基本没了。但游泳一项因毛主席的提倡,被保持下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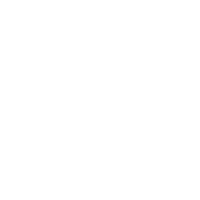
“枪炮声”大作
对住在中南海的孩子们来说,第一个好玩儿的地方是瀛台。这儿的古建筑极具东方色彩。从北面走是汉白玉花桥,登桥而上是灵秀雅致的翔鸾阁,在两边弧形的楼上,既能远眺景山的高亭和北海的白塔,又能俯视静谷的联理柏,还有“芝径缭而曲,云林秀以重”的庭院。再往南是涵元殿,现在是中央领导人经常接待外宾的地方。
穿过月牙门南下,就到了南海边的迎薰亭,小亭三面临水,一端与瀛台相连。但孩子们对瀛台的兴趣,既非亭台楼阁或者湖光月色,也非有关光绪皇帝在此被慈禧囚禁的故事。而是因为,这儿是比毛泽东住所管得更严的地方。曾有孩子试图从玉带桥旱路登“台”,屡屡受挫,被警卫战士毫不留情地赶走。于是瀛台的神秘便勾起了大家的好奇。后来隐约听说那儿有军事设施,更激发了我们探密的决心。
那天我们兵分两路,下中海划船到瀛台登陆,绕过哨兵,来到涵元殿前。只觉眼前一亮,这儿竟有一个偌大的兵器展览,是专向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汇报用的。这些庞然大物,特别是喷气式战斗机是怎样弄到瀛台的,至今我也想不明白。不消说,一帮男孩看到货真价实的飞机大炮就在眼前,自然是喜不自禁。大伙争先恐后,有的爬进飞机坐舱,有的摆弄枪炮。我则坐在一架四联高射机枪座上,摇动手柄,嘴里学着开枪的声音:“哒哒哒哒……”没过一会儿,“枪炮声”便引来四五个警卫战士,对我们进行“搜捕”。我躲在一门120高射炮的帆布罩下,自以为很巧妙,不料慌中有错,碰倒了里面炮弹,声响虽不大,但足以暴露我的藏身之地。
这件事最终被中央办公厅通报。父母觉得很丢人,特别是爸爸,发狠要揍我兄弟二人。当时我们溜之大吉,后来稀里糊涂地不了了之。
偷了一张地图
中南海里第二个好玩儿的地方,是居仁堂、春藕斋、爱翠楼一带。居仁堂是座中西合璧的楼,春藕斋在它的正门南边。都知道只有到了夏秋之季才莲香藕肥,可这儿为什么却叫“春藕”,我一直没得到解释。毛主席的住所是丰泽园,老人家从丰泽园后门出来,沿着中海的马路,走几分钟就到了居仁堂。
附近的四合院永福堂,是彭德怀的故居。
这一带也有山、有水、有楼,解放初居仁堂曾是中央军委作战部的办公地点。在那个尚武的年代,没哪个男孩子不对军事感兴趣。后来赶上军委机关从这儿搬出,我们几个孩子便走进去搜检了半天,但没发现太多好东西可玩。有人从沙盘上拿了几个铝制小坦克模型,我从墙上的一幅大地图摘下两块,好像是云南一带的地图。我们刚走出居仁堂,迎面正碰上彭德怀元帅。他平时很严肃,总绷着脸,不怎么理人。从朝鲜回来后,大家都知道他战功卓著,又多了几分敬畏。那天邂逅,我们因为做贼心虚,高一声低一声地说:“彭伯伯好……”然后夺路便走。记得当时彭总心情挺好,居然也含笑点头。
后来,我用那两块印着地图的纸包了书皮,祸事便因此而起。因为是比例很大的专用地图,属于机密文件,中办追查下来,我很快被“缉拿归案”,乖乖交出。爸爸因为出差广东,鞭长莫及。我虽免了当面责骂,但爸爸很快给中办写了检查,自请处分。
我们爱去玩儿的第三个地方,在国务院辖区。因为门诊部从“东八所”迁到了紫光阁的东北角,我们看病拿药,都要穿过游泳池的警戒哨,这儿属于国务院的范围。紫光阁的前面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很适合做检阅台。而对我们玩“打仗”,这里同样是好场地。
一天,我们又在这儿折腾。记不得是谁的主意,旁边楼里窗户上的白绸窗帘被我们扯了下来,绑在竹竿上,当成了“军旗”。这帮孩子在大平台上东奔西跑,上窜下跳,吆三喝四,好不热闹。这时,周恩来总理偏偏从这儿路过。我们又嬉闹了一阵,终于发现了皱着眉头驻足观看的总理,自知又干了件大蠢事,于是分头逃窜,总理这才离开。
没过多久,爸爸把我们兄弟叫到一起,没有责骂,只是语气沉重地说,周总理对国务院的干部有个讲话,大概意思是,紫光阁这个地方是过去皇帝校阅皇室子弟骑射成绩的地方,算是个考场,目的是为了不让皇室子弟荒废武功,丢失祖宗打下的天下。如今我们不能连封建帝王都不如,要教育好干部子女,继承革命事业等等。
先吃饭后记账
记得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家里来客人,常会好奇地打听:在中南海里能不能吃饱饭?听说也是按定量吃,便都将信将疑。
中南海的食堂分小灶、大灶和特灶。毛泽东、周恩来较早进驻,一直是单独开伙。刘少奇、朱德刚搬来时分别住在“卐”廊和永福堂,也单独开伙,后来住进甲一、甲二楼,就集中在西楼吃。彭德怀从朝鲜回国后也在西楼吃饭。所以西楼成了中南海最大的特灶。1959年彭德怀离开中南海,1964年刘少奇搬进林伯渠的宅子,西楼的特灶就只剩朱德一家人吃饭了。
小灶食堂原来在东八所,这是警卫局、管理局和保健处所在地,供中层干部吃饭。困难时期,我家住在居仁堂的西北角,便在这里吃饭。办法是先吃后记账,月底结算。大家都很自觉,吃多少记多少。小孩子也随便吃。后来家里觉得这不利孩子成长,让我们去大食堂吃。大食堂就是大灶,在怀仁堂东北侧,游泳池西边。我们的伙食标准是每月12元,粮食25斤。通常是早餐一个窝头、一碗粥、一碟咸菜。如果能吃一个煎蛋,就属奢华了。中午是米饭炒菜加一碗酱油菜叶汤。自然灾害严重的时候,有过警卫团从内蒙打的黄羊肉,加上土豆、红薯、黄豆、玉米碜,品种多样,还有当时发明的小球藻、人造肉等等,也没觉得怎么挨过饿。
在大灶吃饭的一大乐趣,是一帮孩子可以聚在一起胡作非为,而且可以彼此丰富食物的品种。不久,中南海机关响应毛主席革命化的号召,许多领导人如刘少奇、朱德同志的子女也都到大灶吃饭,这里更热闹了。食堂北侧是个大舞台,供机关干部听报告开会用,平时就成了孩子们打闹嬉戏的地方,大人虽不满意,倒也不管。但好景不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朱德夫人康克卿,李富春夫人蔡畅等来到大灶吃饭,孩子们多了几分敬畏,少了几分顽皮,食堂里气氛安静多了。
中南海里也有不少可供食用的植物。朱德不仅自己种植瓜菜,也是辨识和食用野菜的高手。有时周日去他家作客,一般是爸爸陪朱老总和其他客人聊天,我们便跟着康克清在院子里摘野菜。午饭的菜谱常常是凉拌马齿苋、野苋菜汤、灰灰菜或者荠菜馅饺子之类。此外,我们还吃过槐花、榆钱、柳芽、杨花穗……
中南海还有水果,如桑椹、葡萄、梨、桃、海棠、樱桃、柿子等等。陈伯达和李克农家院外各有一棵桑椹树,夏天一到,我们一帮孩子就爬房顶摘桑椹吃。只要看嘴的颜色,就知道是吃了谁家的桑椹,因为陈伯达家是紫桑椹,李克农家是白桑椹。周总理院里有著名的海堂,但中看不中吃。它花开艳丽,果实粉红,吃起来涩涩的。没有朱德家门口的梨树好。梨子个儿大水多,咬一口脆脆甜甜的。不过偷梨的风险大,警卫员一眼能认出是谁家的孩子,一旦被抓,“家法”难逃,所以我们轻易不敢造次。杨尚昆家院里的樱桃最诱人。红如玛瑙,紫如紫檀,光华玉润,吃在嘴里酸酸甜甜,沁人心脾,所以遭劫率最高,杨尚昆屡禁不止。有一次我们偷樱桃,他因此被扰了清梦,便站在窗前厉声喝斥,但也没有采取什么组织措施或行政手段。孩子们后来仍然故我,照偷不误。
陈毅钓到鱼又放了
在吃的问题上,对孩子们诱惑最大的还有中南海湖里的鱼虾。建国之初,中南海曾大规模疏浚过一次,当时并没放养鱼虾。后来从北海那边钻过来一些小鱼苗,所以有时也能捞到些白条鱼和小虾。捞虾的办法很简单:找个大筐,铺上烂草,放上些牛羊猪的头骨或架骨,压块石头,沉入湖中,过一段时间拉出来,把钻到筐里的虾拣出,把筐再沉入湖中。循环反复如此而已。
开始时,陈毅、贺龙等领导人也喜欢在中南海湖边散步和垂钓。后来,管理局在湖里放养了鱼苗,就在湖边树了块牌子,醒目地写上“禁止钓鱼”。在这之后的一天,我们正在玩耍,见陈毅来到了湖边。工作人员拿着风衣和马扎走在前面,陈老总拎着小水桶和钓竿跟在后面。工作人员眼尖,发现那块牌子后,大概是为了不扫老总的兴,马上将风衣搭在上边,老总当然就看不见了。大约一个多小时,陈毅钓上了四五条鱼,很是满意,打算撤退。他把水桶和马扎交给工作人员,自己去取风衣,这才看到牌子上的字。于是脸沉了下来指着牌子问工作人员:“怎么回事?念念这几个字!”工作人员傻笑着没敢说话。他接着说:“这几个字念‘禁止钓鱼’,懂吗!也包括我。”说完,让工作人员把鱼又放回湖里。几十年了,那天的事我至今仍历历在目。
过年
在中南海里过年,是小时候最盼望、也是最快乐的事情。因为过节期间可以尽情玩闹、吃喝,内容广泛。更重要的是,谁过年都图个喜兴,所以家里的管制自然也就大大松懈了。说起来,过节其实也很简单,无非一个吃,一个玩。
先说说吃。每到新年和春节,每家都会领到一大把花花绿绿的票证。凭它就可以到大灶或小灶食堂领取生熟食品、水果,点心及其他副食品。这些东西在今天是人们司空见惯的,可当时对我们每月12元伙食标准的孩子却是极大的诱惑。平时从不做家务的人,年前也会主动请缨,到食堂排队领吃的东西。排队的人虽多,大人们都很有对心,不像孩子们那样张狂。
我印象比较深的有3个人。一个是中办秘书室的戚本禹。他总戴着眼镜,很深沉的样子。他女儿雅雅和我妹妹是同学。戚待人很和气,谁排队“夹塞儿”到他前面,他也不吭声,皱皱眉头就忍了。第二个是中办俄文组的阎明复,说话带东北口音,喜欢和小孩逗着玩,一天到晚乐呵呵的。还有一个是中办工业组的张道峰。他可不像前两人,看见小孩子吵吵嚷嚷,往往要呵斥一通。我们虽不怕,但多少有些怵头。张后来犯了错误,被逐出中南海。
没成家的干部和父母出差的孩子们,过节时可以领到会餐券,去大灶食堂聚餐。聚餐一般比平时多四五个菜,以肉菜为主,价格特便宜,比如砂锅鸭块一元五角,烧鸡二元,茅台酒五元一瓶……这在今天自然是难以想象的。
朱德家里人很多。他在老家的兄弟,每户都有一个小孩来京,由他抚养。这样,老总的侄孙(女)就有了七八个,加朱琦和朱敏的孩子,其热闹程度可想而知。当时,朱家的大师傅老邓只给朱老总和康妈妈两人作饭。孩子们要吃什么,只要有东西,全凭自己动手去做。朱德兴致高时,偶尔也会露一手。我最难忘的,是他做的水果和蔬菜沙拉。吃年饭时,饭菜虽摆了一大桌,但朱德只吃自己的饭——通常是五花肉、青菜、豆制品,有时有鱼,再加上豆瓣酱和米饭。爸爸说,朱老总在外视察也这样吃饭,当地党政军领导招待他,满桌山珍海味或西餐大菜,但他只吃邓师傅做的简单饭菜。
叫江青“阿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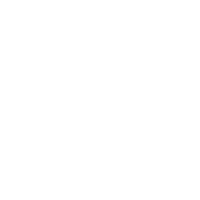
在紫光阁前留影
在中南海过年,能让孩子们享受的项目主要有三种。第一是机关干部和警卫团的人自娱自乐的联欢。娱乐项目有奖,奖品大多为简单日用品如牙膏牙刷毛巾之类,也有糖果。二是专业文艺团体的演出。这些演出一般是在怀仁堂、西楼、春藕斋、国务院小礼堂或紫光阁,主要是戏剧、歌舞。三是看电影。让中南海的孩子们看电影,常常是由康克清、蔡畅、邓颖超、王光美等中央领导的夫人组织,多是演动画片。看电影时往往备有糖、瓜子和汽水,算是有吃有喝,让我们开心不已。除此之外,有时还有舞会。这当然是为大人举办的,小孩子不感兴趣。那时候,中南海的孩子对中央领导的夫人都以“妈妈”相称,如“康妈妈”、“蔡妈妈”、“邓妈妈”等等。唯独称江青为“阿姨”。这大概是因为她给人的印象是“和蔼不可亲”,又是主席夫人,所以敬而远之。
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听侯宝林说相声。那年过春节,西楼开舞会,我正好从外边路过,忽然发现侯宝林一个人在门口,还念念有词。我知道,待会儿一定有他的节目。于是想进去占个位子听听,不料被服务员拦住:“一会儿主席来,你又不跳舞,别进去添乱了。”无奈之余,我便去找侯宝林套瓷,假装和他特熟地聊了一阵。到该上场了,侯大师对服务人员点点头,说;“一块儿的。”就这样,我顺利地进去了。时隔多年,一个偶然机会,我在全国政协礼堂又见到了侯大师,他当然不会记得我。我提起了那年的事,他笑着说:“其实我知道咱俩谁也不认识谁。你喜欢听我的相声,我也高兴。”
打麻雀
新中国成立后,中南海成为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从而也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发源地。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直到“文革”,红墙外面热火朝天,中南海里也不清静。
那年全国搞“除四害”运动,麻雀是其中一害。由于麻雀会飞,“除”起来很困难,于是北京市搞了一个统一行动,全民动员,敲锣打鼓地哄麻雀,让它不敢停留,最后累死,或者飞不动时被人捕捉。今天看来很可笑的事,当初可是十分严肃地被一丝不苟地执行了。
只是在中南海,遇到一点小麻烦:这样搞,麻雀肯定是不安生了,毛主席怎么办?老人家喜欢晚上办公看书,白天睡觉,全北京城折腾都没关系,在中南海里吵到他可不行。于是管理局想了个法儿,让工作人员拿着竹竿,绑上红布,在中南海里挥舞,吓唬麻雀。结果,大人们像傻子一样的举动,成了我们小孩子最名正言顺的游戏,甚至原来禁止打弹弓的规矩,也在不许打碎玻璃和电线瓷瓶的前提下解禁了。至于麻雀被累死、吓死了多少,大概无人知道。
毛主席曾经号召全国人民“到江河湖海去游泳”,也在老干部中形成了十分普及的运动。毕竟,它既锻炼身体,又是一种放松休息的方式。中南海的游泳池是中办和国务院的分界线,露天游泳池在国务院辖区,室内游泳池在中办辖区。毛主席工作累了,就到游泳池游泳,大家各不相干。有时老人家也在游泳池接见外宾,这时闲杂人员要一律回避。后来毛主席离开丰泽园,干脆搬到游泳池住去了。此后,管理局在中海湖里搭建了两个平台,让工作人员到湖里游泳。这对小孩来讲,简直是天大的喜讯,因为在游泳池要花两毛钱,在湖里游则分文不收,随便得很。只是到了“文革”时期,就基本上停顿了。
大字报
每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在中南海里都有反应,这集中体现在大字报上。一般贴大字报的区域是国务院食堂和中南海食堂,以及警卫团几个中队驻地的围墙处。
邓小平住在庆云堂的含秀轩,和陈毅是邻居,都在大食堂的西南;董必武和王稼祥住在怀仁堂东侧,在食堂的正南。他们散步时,就溜达着看大字报。当时大字报的内容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上纲上线却厉害。反右时,一个王姓小伙伴的父亲被贴了大字报,说是用公家信封装人民币带回老家,家乡人看到信封是中共中央落款,就想托他家人向毛主席反映情况,请他家人白坐了一回长途汽车,没买票。当时这位王叔叔当笑话讲了,却被人上纲上线说成动机不纯,狐假虎威,招摇撞骗,破坏中央机关威信云云。我们几个孩子知道了,想去撕掉,正好几位领导人在看那张大字报,我们才没敢造次。记得当时王稼祥看这张大字报时观而不语,董必武又点头又是摇头,看不出什么态度。只有邓小平说了句:“还很尖锐的嘛”,听不出是褒还是贬。
“文革”中,大字报也由浅入深。开始是响应型的,诸如“坚决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类,还没有指名道姓,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大字报说朱老总是“大军阀,黑司令”,一些工作人员也明显地欺负朱老总夫妇。朱让我父亲和一组联系,想约毛主席谈谈,回话说“主席很忙”。这事弄得父亲很紧张,不知道主席对朱会有什么动作。我父亲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也是坚定的共产党人。他生怕跟不上主席的思想,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之后我响应毛主席号召下乡插队,父亲去中办五七干校,全家从此离开中南海。●
文/沈小雨